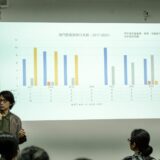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東西》:人生「話」長卻又苦短
《東西》是一齣動用十六位女演員的舞台劇,由本澳劇界歷史較久的「曉角劇團」所創作。正因為歷史悠久,所以演員選角方面,也起用了不同年齡層的女角色,由三十歲至六十五歲的演員擔演。
《東西》主要講述四位過去一起讀女校的中學舊同學與一名已移居外地的同學,透過視像通訊一起遊歷澳門,期間除感嘆澳門數十年間的變化,亦穿插各人回憶,並由較年輕的演員飾演四人在中學階段的情景,再以一大班舊同學相聚的情況作結。
劇本結構看似簡單,但呈現方式卻很考工夫。筆者尤其欣賞最初使用全白幕,把飾演四人年輕時期的演員隱藏在後方,其後四人才上前表演,輕易地令人意會到四名較年輕的演員是屬於回憶中的人物;更欣賞的是鋪排,每一名年長女角對應年輕的自己進入回憶後,以一年長角色與三年輕角色互動,讓人意會到年長的自己回頭看年輕的自己,當年是如何與同學們相處。如此八人分別交替演出,除了帶出回憶感,亦令觀眾有代入感,同時更帶出各人所重視的回憶到底是什麼。再來是穿插不少歌曲,演員的演唱表現令氣氛眼前一亮,令人享受。
在劇情的推進中,可以看到回憶量的龐大,諸如校裙膝上三寸、頭髮過肩要綁起等校規;再到校內活動如何合作、升學抉擇、一起遊玩去識男仔、拍拖結婚生子等細節,猶如細數家珍一樣,即使觀眾不是就讀女校,若能體會當中塑造的學生時代,相信也會共鳴地尋找自己腦海深處,屬於孩提時代的回憶。直到劇中最後,有朋友因病即將接受安樂死的事件,去感嘆人生之中能說著回憶的故事可以很長,但生命卻又苦短。
至於有待改進的地方,就是演員做獨腳戲的開場白,故事內容也許感人,但表達/表演沉悶,令人感到突兀,而沒有代入感,其後間中出現的獨腳戲間場皆是如此,令人出戲。
至於正式開場的打麻雀情節,起初在舞台僅有一張麻雀枱,感覺新穎,期待舞台如何展現打麻雀的情況,但期間,僅是以打麻雀之間的閒談來帶出整體人物性格、背景,過程冗長,同時感受到演員有嘗試記憶對白的情況。
然後是一眾十多名演員共聚,本來互相帶有比拼生活的情節,的確可以感受到舊同學之間已陌生,以至要鬥一下誰過得好的感覺;但是相對無言,以笑遮掩尷尬的次數有點過火了,時間過長,令人感到是演員忘了對白,而不是戲劇效果。
綜觀全劇,令人動容的不是故事內容,而是令人反思著日後會有多少人一起和自己再次想起那些年的小故事?現在的自己已和過去的伙伴失聯多久?腦海中的朋友到底有沒有變了一個樣?
「我不怕死亡,只怕被人遺忘」,又有誰知道未來的自己,在回望人生期間是孤寂還是仍與同伴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