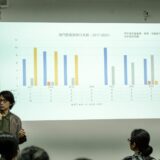星光下的置換與突變
茫茫寰宇,萬籟俱寂……一棵大白菜孤獨佇立大地,他每天能做的就是仰望星空,故常感寂寞。一隻毛毛蟲在他的世界裡出現了,毛毛蟲要吃白菜,白菜毫不吝嗇讓她多吃。在白菜的哺育下毛毛蟲日漸長大變蝴蝶飛去。留下衰老的白菜繼續仰望星空。
置換
這是改編自陳敢權同名原著的兒童劇《星光下的蛻變》,同樣是說愛與犧牲的主題,但劇中人物關係已從兩性置換為兩代了。「置換」為主題傳達帶來一定優勢,但也帶來風險。劇中大白菜身兼愛、付出與教育者的角色,毛毛蟲就成了對啥都好奇,像海綿般吸水,同時也更期待自己快快變化長大的孩子了。這個置換更適合兒童劇的需要,因為兒童還沒來得及經歷兩性感情體驗,親子關係對兒童來說更好理解。另外,所謂「愛與犧牲」的主題,戲劇也試圖探索其「不望回報的愛的付出」的可能境界,這個「不望回報」的動作放在「父母對子女的付出」這樣的結構動作關係裡,顯然比放在兩性關係裡更有說服力。可以說,人物關係的置換倒是將原著的兩難悖論解決了。
定律
定律是這部劇的關鍵詞之一。大白菜的定律是被毛毛蟲吃,毛毛蟲的定律是變成蝴蝶。在原著中,毛毛蟲只在大白菜的夢中變蝴蝶。她最後向大白菜表態:不願變蝴蝶,不願離開大白菜;然後兩人相擁同望星空,劇終。這個開放性的結局沒有解決毛毛蟲的兩難處境:吃大白菜就會變蝴蝶飛走,不吃就要結束生命。原著的結束處有一句舞臺提示:天上的星光,明滅之際,演形砌成了一隻蝴蝶的模樣。這個提示似乎在暗示劇中人難逃定律,最終要分開。但這個提示可能過於隱晦,當導演在舞臺上把它表現出來時,很可能要被觀眾理解為不是真變,而只是一種主觀的、精神上的蛻變。
結局
在本次演出中,莫嘉紋導演改動了結局,毛毛蟲終於變蝴蝶飛走,大白菜雖不捨卻只能接受定律,然後彼此約定日後共望星空為念。這個改動符合兒童劇的美滿結局需要,雖然這是以大白菜的孤獨為代價,但大白菜對定律的接受與坦然又寬慰了觀眾的不安心緒,而這正是戲劇要歌頌的偉大——上一代的犧牲成就下一代的美麗與高飛。
星空
這是個音樂劇,雖然舞蹈很少,也沒有大排場,但勝在歌曲動聽,演員也都能唱。同時,現場鋼琴伴奏也提升了演出的規格。其中一場利用黑箱劇場牆體做的星光裝置別具匠心:當大白菜與毛毛蟲唱起「望星空」歌曲時,觀眾被吸引也仰頭同望,恍惚有一絲置身星空感覺,因為從牆壁到天花板都佈滿發亮星星。其實這是一個簡單裝置,卻帶來一種意境與感受,從中可見其巧思。
突變
在蛻變蝴蝶這一段,導演安排了另一演員(舞蹈員)扮演蝴蝶出來跳舞,這個安排頗有可議之處。在演後與導演交流得知原意是讓毛毛蟲「跳出來」,以另一自我與大白菜一起見證這美麗的一刻。但這一手法對兒童的理解來說似乎有點兒為難了。可更大的問題是,這樣的安排已破壞了全劇原來統一有序的藝術策略:飾演毛毛蟲的張可恩最早是以布袋偶演員身份出場的,那時她操作一條代表新生的小毛蟲布偶。蟲吃白菜要長大,所以到了下一場她換了一條大毛蟲布偶。她第三次出場時不帶布偶,因為她本身就是毛蟲——毛蟲長得與人一樣大了。可以說,這由小到大、由蟲到人的變化清清楚楚有趣生動。正當小朋友滿心期待可愛親切的可恩姐姐變成美麗蝴蝶時,卻冷不防殺出另一陌生人上身蝴蝶:這個蛻變變突變,帶來的可不只是尷尬而已,問問小朋友感受,或許還包含著失望與不解。
不解
說到小朋友的不解,其實不光是蝴蝶為何要上身陌生人。此劇歌頌父母的愛與犧牲以成就孩子的主題,對幼兒來說或許就如空氣一般,他們每分鐘都在享用,但他們怎麼知道它存在的意義呢?網上讀到二觀眾——網名王大香網友,與她孩子小熊的對話:
「條毛毛蟲好有問題!」
條毛?
「我說他問太多問題了啦!」
喔,例如呢?
「他問農夫是什麼,拜託他怎麼可能不知道!他天天都在田裡吃農夫的菜耶!」
喔喔,好像也是喔。
「還有明明是給小朋友的戲,可是有很多小朋友不懂的東西。例如說『定律』這個辭,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喔,那你想知道嗎?
「也是想啦,整齣戲我就一直想是什麼意思就好了!」
那你喜歡嗎?
「喜歡呀!」
孩子的評語傳達了兩個資訊,一是不太看懂戲劇,並且對戲劇的部分內容的邏輯性有所質疑;二是雖不太看懂但還是喜歡此劇。這似乎解釋了,現在有些兒童劇的製作,越來越喜歡擁抱那些從內容上來看是正能量積極向上的人生道理,但對兒童來說卻是深奧難懂之主題。而這些製作卻還是高朋滿座。因為「正能量積極向上的人生道理」總讓父母趨之若鶩。就像本劇的主題。為人父母誰不希望讓孩子看一場戲來獲得娛樂,同時又獲得有益成長的人生道理,進而理解父母對自己的愛與犧牲呢?但父母們不妨問自己,咱們是啥時候意識到父母的「愛與犧牲」呢?還不是自己做了父母的時候,至少是自己成年以後吧?所以這事情急得來嗎?對兒童劇製作者來說,只要在談人生道理的內容裡揉入兒童元素:歌、舞、色彩、遊戲、趣味等來抓住兒童觀眾的注意力,也就是包裝得像兒童劇,那就能賣得不錯了。
迷思
一些兒童劇團在演後收集觀眾的意見匯總發表,但他們收集到的只是父母的回饋。這些回饋往往大力肯定戲劇的美學風格或思想旨趣,這其實只是表達了父母的良好願望:希望孩子看到的或被傳授的是一種「好」的內容。於是這種回饋可能會矇蔽業者發現製作的問題,因為這些內容在臺上出現時未必是兒童能感知或感興趣的。這也是目前有些兒童劇業者的迷思:服務對象已從兒童置換為兒童的金主了。
歧義
回到本劇,以「大白菜就是要被毛毛蟲吃」之定律來烘托愛與犧牲主題,本意讓觀眾頓悟親情之偉大,但結果可能也會走向反面:強化了「父母為子女付出是理所當然的」,不要奢望子女回報。這讓「啃老族」獲得理論根據,可以啃得心安理得了;這就是本文開頭所謂之風險,人物關係置換後影響了戲劇的解讀:導致主題也出現了歧義。
再者,「被毛毛蟲吃」其實也不是大白菜的唯一定律,或第一定律。因為大白菜並非野菜,是農夫的辛勞結晶,所以第一定律應該是:被整棵割下然後被人類吃掉。這樣說,就意味著大白菜最後在地裡枯黃,對稍有生活常識的兒童來說也未免是個困惑了。
本劇的舞臺製作表現均衡,其中音樂與表演(尤其主演張可恩)比較突出;可惜在改編上有欠周密,顧此失彼,雖擴展了戲劇主題,卻引發更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