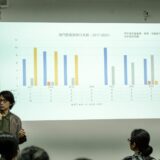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可以睡覺》:參與式劇場裡的春秋筆法
「明日和合製作所」和楊彬共同打造的《可以睡覺》是一個參與式劇場,當然這並非「藝穗節」中的唯一一個,對於大部份習慣黑盒劇場或是鏡框式舞台的觀眾而言,「參與式劇場」聽起來彷彿是個新鮮的噱頭,通常這種狀況總有人延伸出是否生搬硬套的疑慮來,但不管是先有《可以睡覺》還是參與式劇場,我認為之於這個演出來說,都是合適的安排。
首先,相比起《鄉愁的妮雅廬》和《紅兔子.白兔子》這種壁壘分明的演出,《可以睡覺》本身就是以婉轉和間接的方式來傳達訊息,把「饒宗頤學藝館」翻轉成酒店,在「睡覺」前驅使觀眾進行各種既有趣又不免繁瑣的「客房服務」,從中賺取代幣來購買他人的服務甚至是抽獎活動,反向質問亢奮雀躍的觀眾是否忘記了睡覺最單純的本義。
也許是模糊了觀眾和演員之間的界限,安坐在觀眾席上聚精會神地解讀舞台上的訊息,這種劇場本來「要說些甚麼」的前提似乎也在嘻嘻哈哈的演出中被隱去,從這個觀點切入,《可以睡覺》說穿了其實只是客觀地為一眾觀眾提供了一個參與「酒店主題角色扮演遊戲」的機會而已,因此能夠供觀眾解讀劇作原意或是引起思考的線索並不多,因此演出的名稱「可以睡覺」這四字便是串連起整個演出的重要脈絡。
客觀地呈現一個冠以「可以睡覺」之名,所有細節都圍繞著「睡覺」的場景,反諷現今關於「睡覺」的種種不正常現象,如果把這一切轉化為文字,應當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中的春秋筆法,不直接棒喝問題所在,只用微言大義吸引觀眾在過程中或事後思索。而更重要的是,參與式劇場加強觀眾體驗的特點,在當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可以睡覺》背後所謂的思考,事實上是要求觀眾自我反省自己的睡眠是否也如此荒誕,而參與式劇場令觀眾在演出的過程中無法抽身於外。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將三個小時的時間「困」在「饒宗頤學藝館」中,觀眾怎麼也應該對這「亢奮的睡覺」有一定感悟。然而在具體執行上,把六名觀眾安排成一個小組,加上四周黑漆漆的氛圍無疑是深化了團體遊戲的體驗,不少觀眾事後都把「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或「很高興認識了新朋友」當成是《可以睡覺》的褒獎之詞,這又不免有若干誤導觀眾抓錯用神的可能了。
*本文作者為第十七屆澳門城市藝穗節特約藝評人
*原文於2018年3月21日原載於「匯澳傳媒.RECAP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