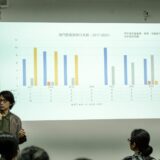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海盜婆》的「大同精神」與社區關懷
作為遊客,甚至是本地澳門居民,你們對路環的印象是什麼?是安德魯的葡撻、十月初五馬路的河岸、還是打卡必到的荔枝碗舊船廠?對非路環居民來說,路環或許是一個周末的旅遊景點,但對進駐了路環差不多兩年的「滾動傀儡另類劇場」來說,路環還有很多「寶藏據點」和人文情懷等着你去挖掘。
在這個中秋節期間,「滾動傀儡另類劇場」(下簡稱「滾動」)聯同從墨西哥遠道而來的「墨西哥繩索劇團」,共同演出了「大人細路一起看系列」環境親子偶劇《海盜婆》,運用偶物、形體和面具等元素,帶領觀眾遊走於路環的巷弄間,展開了一段尋「寶」之旅,探索路環背後的故事。演出不單讓筆者擴闊眼界,發現了很多平時不常經過的路,深入整個路環市區的肌理,還和當地街坊鄰里打成一片,確實體驗了不少人情味。
《海》的創作緣起來自於導演林婷婷自身對路環的生活體驗。在「滾動」剛搬到這個新環境後,發現人口分佈多為獨居老人和外籍勞工,他們的家人或朋友偶爾回來探望,便又離他們而去;又受到李展鵬的《隱形澳門》所啟發,於是靈機一觸,想訴說這群「隱形人口」的故事。話雖如此,表面看來是為弱勢發聲,但背後所表達的,卻是有著大同世界的普世價值。
劇情起初分為四條線,每條線分別講述婆婆、小狗和東南亞裔父女四名角色背後的故事;觀眾在恩尼斯花園集合後,便被分為紅、黃、藍、綠四種顏色的隊伍,由四名小燕子操偶師帶著遊走於四條不同的路線。筆者跟隨的是東南亞裔女兒的故事;她與觀眾在小巷中拾獲精美的石頭,又走到沙灘和父親會面。這條故事支線描述他們離鄉別井後時卻惦掛著家人;此外,他們淨灘之舉又反映了他對海洋的愛惜之情,正如東南亞裔女兒說道,「Whatever you give the sea, the sea will give you back」,頗有環保主義和佛教因果業力的意味。觀眾有如他們生活的旁觀者,以客觀的眼光了解外來人口作為「他者」在澳門的生活點滴。觀眾隨後在多個定點欣賞演出片段。
「海盜婆」和她那名不是經常在身邊的孫仔見面,但他卻沉醉於手機遊戲當中。她見狀,想為他找來一把「海盜劍」,藉此取悅他,於是便展開了一段尋寶之旅。在旅程中,她與東南亞裔父女因偷竊鹹魚而爭執,又遇到活潑的自來狗。在她夢中,她幻想/想起了自己曾經是海盜的父輩,對抗入侵地盤的海軍。最後,各隊觀眾進入臨時演出空間,那是「海盜婆」的住處,經一輪打鬧之後,「海盜婆」取回劍,但孫仔卻對其無甚興趣。反而在與東南亞裔女兒的打鬧中,漸漸懂得陪伴才是難能可貴的「寶藏」。
在澳墨兩地的合作之中,當要考慮到演出語言的問題,是使用英語、墨西哥語、還是廣東話?答案是以形體動作為主軸,混雜少量各種語言。動作可算是世界語言,不同國籍或年齡的人士都能大致明瞭一些共通的身體語言。袁一豪飾演的「海盜婆」與歐志恆飾演的孫仔,見面時互相玩耍,時而揹著對方、時而又以身體推動對方,做出小丑式的形體表演,逗得觀眾十分歡喜。而在與東南亞裔父親爭魚那場戲中,兩人交替拋耍著由棍棒造成的鹹魚道具,也贏得不少掌聲。角色有時也會使用隻言片語來表達意圖,例如「婆婆」、「孫仔」的互相稱呼;海盜婆控訴外來者,「你這邦『嘰哩咕嚕』來搶我地盤」;在送禮物時說道「婆婆給」、「媽媽給」等,讓觀眾(尤其小朋友)能夠盡量理解劇情。由此可見,以形體動作為主、配合少量語言為輔的溝通媒體和娛樂形式頗為成功。但是,筆者認為東南亞裔女兒在巷子裡的單獨劇情稍嫌模糊,只記得她與小孩互動、跳躍,而不知此舉欲帶出之情節;另一方面,形體和偶物元素的特點是「此時此地」,即難以回憶歷史,也難作深度哲思。
場刊的故事簡介提到,「路上的一事一物,喚醒阿婆早已遺忘的童年記憶,彷彿回到祖父輩傳說中的輝煌年代⋯⋯」可見劇情與「海盜婆」的回憶和父輩的歷史相關。於向海公園的那場戲中,阿婆睡著了,然後進入了夢境世界中。她自己化身為海盜,而原本飾演東南亞裔父女的演員Ana和Diego則成為海軍,彼此展開決鬥;帷幕搭成的布偶劇場亦豐富了她奇特的幻想。她一覺醒來之後,尋覓已久的「海盜劍」便出現在身旁。在沒有語言的情況之下,似乎難以將回憶、歷史與演出相連結,觀眾或可將此場戲解讀成阿婆的想像,如此一來,便使她的仇外動機(或受父輩的海盜大敘事影響)與路環的歷史面向黯然失色。此外,「環境劇場」的演出選址也涉及美學取向。在公園不遠處,便是紀念1910年「路環慘案」的「打海盜紀念碑」,既然劇情與海盜有關,演出與此象徵物或許有某程度上的交集。向海公園之選,筆者以為,注重其易於搭建舞台的功能性多於其歷史意涵,故失卻了與社區歷史對話之機。
「滾動」精於運用「偶」和「物」的元素於劇場當中,而在此面對親子作為觀眾群的演出中,更見團隊在戲劇構作上的創意。演出中的所有角色皆戴上面具,這樣除了能解決演員與角色年齡相異的問題,也為整場表演注入了童話色彩。值得留意的是,導演和道具製作者考慮到墨西哥演員與東南亞人士輪廓不同,所以東南亞裔父女的面具經過精巧的調整;阿婆和孫仔的面具手工也相當精緻,讓演員戴上後完全進入了角色。圓潤的顴骨和粉粉的腮紅充滿喜感,教人聯想起「麵包超人」,特別討小朋友歡心。此外,歐志恆是小狗的主要操偶師,無論在活動、神態和叫聲等方面,他都模仿得絲絲入扣,可謂人狗合一;其與阿婆的搞鬼情節,更教人難忘,使得小狗此偶成為了是次演出的一大亮點。
提到偶,四條路線的小燕子操偶師,黎梓盈、廖紫欣、歐翠欣和黃苑瑩,看似微不足道,但卻相當重要。在行走當中,小燕子們會吱吱作響,引領觀眾走到指定的方向;此外,她們也會在特定的地點提示觀眾一些特別的「看點」,例如屋簷下的燕子巢、路環藝文空間和造船分會等。言則,她們是引路者,也是觀眾與社區的連繫者;據說在晚上演出中會換成螢火蟲,是為觀眾的照明者。在演出中途,突然下起雨來。工作人員很細心,馬上把臨時幕棚搬來,給觀眾擋雨。此時小燕子們還會與小朋友互動,藉此維持著演出歡樂的氣氛。不足之處是,在觀眾秩序的安排上可能稍有失誤,以致隊伍到達演出點的時間不同,使一些觀眾呆等了一會兒,也有觀眾因在途中久候而遲看了一些演出。
在戶外演出完畢後,眾隊伍走進一個臨時裝修而成的演出空間,此處原是路環居民添根叔的雜物房,後來把雜物搬走,慷慨地供演出使用;又多得「墨西哥繩索劇團」的創意,把它變成能夠演出的場地。他們物盡其用,把沒用的紅酒箱設計成小狗、奶粉罐變成燈罩、把廢棄的竹竿和木材搭成舞台,也安裝了電風扇給觀眾涼快。舞台設計師José把「海盜婆」的房間設計成船艙模樣,裝置了掛畫、繩索、木枱甚至船窗,使觀眾尤如進入了她內心的海盜世界。此房間機關重重,燕子會從鳥巢探頭而入、「海盜婆」能在木柵下躲藏、角色也可挽著繩索在空中盤旋,如此別出心裁之設計,讓觀眾看得又驚又喜。
筆者不禁想起,文化部門忽略了一眾本地出色的劇場藝術家,文化支持傾斜於外來藝術家為主導的「大師級作品」,對培育本地人才無甚幫助;另外,自澳門文化中心建成以來,官方再無新建恆常的戲劇演出場地。相反,藝術團體自發或與民間合作,則勉強開拓了不少演出空間,作為一個時常高叫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促進藝術發展的政府,對藝術界的演出資助和場地供應嚴重不足,理應感到自愧不如、無地自容。
《海》在中秋節期間上演,描述了「海盜婆」由一個厭世倔強、獨居路環、思想相對封閉的「本土派」,通過與孫仔、小狗和外籍人士的經歷,明白到相互理解和尊重的重要性,原來一直尋覓的「寶物」乃是陪伴和愛,而愛不分種族甚至物種,很切合中秋團圓之意味;另一方面,在澳墨藝團的交流中,「滾動」從「繩索劇團」身上受益匪淺,在製偶方法、面具物料、舞台搭構、乃至小丑式的形體表演等方面都有所得著,而「繩索劇團」又從「滾動」身上學會了他們獨特的劇場美學。從演出內容、甚至劇場政治,整個製作在在體現了藝術無國界的「大同精神」。觀眾看完演出後,頸上掛著周邊汗巾、手上拿著特色場刊,遊走於社區,體會民間情懷。苦苦追求的文化交流、特色旅遊,不就是這樣一回事而已嗎?
* 2019 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評論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