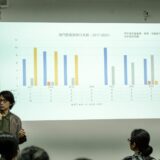在疫情期間思考劇場與公共領域
新冠肺炎疫情自去年年尾起持續擴大,並先後在中國及世界各國蔓延,自「第十九屆澳門城市藝穗節」後不久,特區政府關閉全部藝文設施,一至三月的演出及校園巡演等戲劇活動不是取消便是延期,而今年的澳門藝術節亦宣布取消,澳門劇場界進入了數個月的冰河時期。經一眾劇場工作者與文化局商討後,當局推出多項紓緩措施,包括開放排練室及批准獲資助的本地展演項目可提前在半開放的劇場進行線上直播或錄製演出等製作。在這段離開劇場的日子,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劇場與公共領域的關係。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Christopher Balme)在2014年出版、2019年由白斐嵐譯成繁體中文版的《劇場公共領域》試圖運用尤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概念,分析劇場與公眾的關係,並重新定義劇場在社會的地位。巴爾梅開頭在〈導論〉中便清楚指出他對公共領域概念的定義:「哈伯瑪斯對上概念的定義(特別是其歷史脈絡),不該被理解為集體(collectivity)或空間,而是人們體現的機制(institution)。」換言之,這裡的公共領域不是指真實存在的物理空間,而是可被理解為一種非物理的論述空間。這些空間包括報章或雜誌專欄、評論網站、部落格,更常見的是社交媒體。與書中提及的其他理論家不同,他們把公共領域和在公共空間進行的實驗創作混為一談,而巴爾梅把焦點聚焦在劇場以外的機制。
要理解公共領域這政治概念,巴爾梅把討論放置在古希臘模式和城邦(polis)之上。讀者可以想像希臘公民在劇場相遇、討論戲劇和時政,如巴爾梅在書中所說:「觀眾在一種『高度群體性的集體狀態』中(就算不是酒神式的狂喜)去感受彼此。」不同階級與教育程度的公民聚在一起,形成一種理想的公共領域。而在觀賞劇場演出中,我們受「爭競作用」影響,引發我們激情抗議,但這種激情是可與機制結構的理性辯論相融和的。通過閱讀戲劇評論和進行公共討論,公眾談論某個剛看完的演出,有時舞台情節可能反而不是最重要,更重要的是其引起非劇場圈內的公眾的關注。如何把劇場演出拉到公共領域的視野當中,是機制內的劇場界人士應當思考的問題。在疫情期間,不少劇團仍然見於公共領域中,有的播放以往演出的錄影、有的閱讀兒童繪本、也有的拍攝實驗性演出。這些活動不一定能使他們以工代賑,也一定讓他們累積大量藝術創作的經驗,但藉記者、劇團管理人、評論人等機制內/外的人士推廣,或許能引起公共領域就「劇場藝術是不是滿足人類精神的必需品」,以及「劇場的現場體驗」等這類問題作出反思。
承接著第一章,巴爾梅在第二章以十九、二十世紀的演出宣傳海報或傳單作引子,強調劇場不單通過演出與公眾溝通,而是從派發戲單的一刻就已經開始建構對話,不單發生在戲前,也發生在戲後。不止如此,從每個演出的短期操作的集合來看,一座劇場的歷史便會漸漸浮現。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社交網絡平台早已取代了當年的戲單,巴爾梅樂見此趨勢,並視其為強化劇場與諸眾溝通的工具。隨著社交媒體的部落格的流行,可謂人人都是評論人,公眾享有公平發表意見的權利,而劇場評論的聲音可以更加多元。故此,巴爾梅認為: 「或許劇場公共領域便能觸及真正具社會/政治議題性的廣大公共領域。」筆者偶有看見非恆常性劇場觀看者,看完劇場演出後在社交媒體發表意見,這些段子能否稱得上是評論另當別論,但此風潮一經推廣,劇場便能更常在公共領域出現,諸眾或更常參與討論社會/政治議題。
書中的第三至五章,主要討論劇場搬演具宗教爭議性的演出時,引起了不同宗教和政治組織的抗爭。筆者認為,這幾章建基於歐洲劇場的發展情況,或許沒有與澳門劇場的狀況直接相關聯;第五章探索演出的寬容許可度,雖主要談論宗教和種族議題,但亦有助反思演出內容的限制。
在最後一章〈分散式劇場美學與全球公共領域〉中,巴爾梅分析了幾個通常被歸類為「後戲劇劇場」(postdramatic theatre)的演出,並探討這些演出所帶動的跨國式公共討論。「後戲劇劇場」創作者大多質疑劇場媒介本身,所以他們跳出了劇場的框框,走到諸如街道或天台等非常規性演出場地進行演出,巴爾梅把它們歸為處境式與分散式美學兩類。本章論述了這些特別作品如何在網路產生跨國性的回應。近年不只特定場域劇場(site-specific theatre),就連浸沉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也蔚為風潮,今年以「在地」為主題的「澳門城市藝穗節」,就策劃了《脫單電影院》和《非官方指定路線》,前者強調觀眾參與,而後者則講述地方故事。節中不少演出確實饒富新意,但是,從內容和美學成熟度來看,這些演出是否能引起網路產生回應?
巴爾梅的《劇》的核心主題認為,「劇場得以同時藉論說與爭競形式參與公共領域、言論自由在台上與台下的界線,以及跨文化寛容度之議題。」其運用公共領域概念研究劇場,打開了一個新的學術領域,成為日後研究相關題材的基礎。但是,筆者對書中提出的一點有所質疑。巴爾梅提出歐洲劇場在公共領域中漸漸失去重要地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黑盒劇場創作者太專注於小眾美學,從而忽略了諸眾。然而,黑盒劇場的演出難道就不能引起公眾關注嗎?縱觀澳門近年引起較多討論的,似乎都是黑盒劇場演出,如「卓劇場藝術會」《奧利安娜》、「滾動傀儡另類劇場」的《藥》、以及「石頭公社」的《勞動的人》;反而,大多數巴爾梅定義的「後戲劇劇場」在澳門劇場中都沒有引起相對的回響。說明除了劇場形式外,內容也很重要。話雖如此,《劇》此書讓劇場工作者(或廣義上的劇場界人士)重新發現,劇場不能抽離現實而獨立存在,因此,劇場之事,不單是藝術之事,也涉及社會、政治及經濟等方面;劇場與公共領域有著密切的關係,若然強化此關係,或許便能重新找到劇場的重要性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