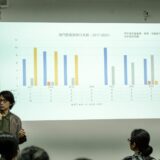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亂世童話》的亂世形象
「破繭計劃協會」結合多名來自港澳的知名創作人,致力「仿照童話故事架構來探討社會及人性等嚴肅課題」(場刊語)。與去年天馬行空的《異色童話》相比,本年的《亂世童話》,其設定、故事、音樂及繪本風格,均朝向一個更為恐怖、暗黑的氛圍。如此來看,作品以「亂世」為名,似是對兵荒馬亂的二O一六,試圖解讀和回應。
故事背景設定於一場駭人聽聞的瘟疫。亂葬崗工人(關若斐飾)困在荒涼的沙堆中進退維艱,既聽命於政府,又苦於內在的求生意志,「留在這裡就是慢慢死,出去(對抗政府)就是立即死」的狀態,似在暗喻香港及澳門近兩年亂世、兩難的困境。可惜,亂葬崗在這裡只作為貫穿故事的工具,如故事一的好心工人,最初仍願意餵瘟疫患者一口水,但在故事二開始之時,竟突然性情大變,講起「執行工作,聽命政府」的大道理,不免讓人錯亂。
而在三個故事(〈收藏家〉、〈努力工作〉及〈餓鬼〉)中,處處可見比對現今澳門的隱喻。如在〈努力工作〉中,在小地方成長、渴望往上攀、為大財團營營役役的女孩詩詩,活脫脫就是一部分澳門人的翻版,這裡的亂世,被解讀為一種財團所控的變態社會,最後詩詩成為了剁人的刀、而非砧版上的肉,似乎只是被變態的資本主義所逼,人心不得不變質的現實選擇。而〈餓鬼〉甚至把「亂世」推到極致,故事設定於受饑荒和戰爭雙重夾擊的困境,配以插畫、音樂、表演,最後揭露張獻忠「易子而食」,然而,除了顯得恐怖外,到底人物是出自怎樣的選擇、亂世與人的關係到底是什麼,均缺乏著墨,於是,在「童話」裡,我們只見亂世的亂,卻看不出亂的道理,最後只落得恐怖、相對俗套的雜錦呈現。
或許是創作形式與導演方法使然,〈收藏家〉在整體演出中,相對顯得溫情:決心守護人們悲傷記憶的記憶收藏家,親手刪除了妻子對女兒的記憶,出走後又回來(為什麼?),最後成功喚回妻子對死去女兒的悲傷記憶(為什麼?)。人對記憶的依戀和排斥,或者可作為〈餓鬼〉裡張獻忠的心理補充,但二者的風格過於迥異,前者非常感人,後者十分恐怖,使得故事之間效果互相消解,無法交流。
至此,《亂世童話》中的亂世,包山包海地涵蓋了各個議題──自然災害的(瘟疫、饑荒)、資本的(變態財團)、生理的(工作、疲勞和消瘦)、心理的(人與記憶、親情)、政治的(社會職責、政商勾結),幾個故事在非常跳躍的時空中互相叠加,難免因過份繁複而失效,因致作品整體看來,顯得凌亂和堆砌。
在〈收藏家〉的「即使悲傷,記憶還是珍貴」的辯證之後,在商業機器使人變質之後,在饑荒與戰爭使人互相吞噬之後,在亂葬崗工人終於迎來「疫苗開發成功」的奇蹟之後,最後用上戰爭、難民的寫實照片(先不論版權問題),似乎作品意圖指涉更大的人類共同災難,但前等亂世的亂尚未得證,此時又加上新的議題,自然顯得更脈絡不明。於是,歌隊最後訴諸「愛」與「家」,當然無法提供足以解救上述種種亂世的出路。
身處亂世,我們都焦慮徬徨,甚至憤怒,在《亂世童話》中,不難看見各創作者的關懷和解讀,但多而混雜的元素,也為調度帶來嚴竣的挑戰。當各故事均被簡化、組合,感官剌激過於強大,到最後,觀眾只能體現溫情或恐怖,而要體現亂世、解讀社會,過份便捷的出路有時相當危險──它使我們無法看清其亂,走到另一個死胡同。如同最後,敘利亞小童的照片,被放映成斗大影像,置於舞台之上,再多的愛、再多的溫情,我們流淚、我們憤怒,卻只顯得無能為力,無路可去。
作者為「第二十七屆澳門藝術節」特約藝評人(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