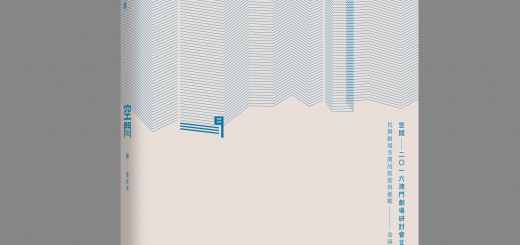如花又如霧──《鏡花轉》所呈現的失焦
近日,台灣、澳門和馬來西亞三地劇團聯合製作,由法國「陽光劇團」(Theatre Du Soleil)演員Shaghayegh Beheshti為總導演的作品《鏡花轉 Kaléidoscope》,引起不少議論,各種意見紛陳的討論,或許正好可作為我們省思己身的參照。
令人感興趣的是場刊裡所共同提及的──「追尋島嶼的記憶」,這一範圍廣濶的點題,似乎為三地(台灣、澳門與馬來西亞)的文化相遇預設了一些議題脈絡,畢竟三地是看似相近又有著許多微妙差異的華文城市,在這題旨中可能有著迥然相異的內容與感受。「島嶼」對澳門來說較不常用,除了地理位置,還可能指涉特有的政經狀況或邊緣的文化身分,「記憶」似乎是私密的,但同時也令人聯想到城市的前世今生,在葡人管治的過去或是今天非自主的自治,可能有著相近的陌生無感,我們可以追尋的又是什麼。
然而這接近三小時的演出(含中場休息十五分鐘),卻只有使我的疑問不斷累積。場景果真如萬花筒(Kaléidoscope)般轉過不停,一幕幕畫面也確是用心設計,有時像是夢中的場景,有時又是戲中戲,這樣的設定可能是有趣的,然而文本與角色的設定,卻始終無法找到脈絡,快速變換的內容讓情感一直處於疏離狀態,一幕幕特別挑選出來的生命片段,當中的洞見模糊不清,對多個段落難以產生較為深刻的感受,以至台上演員的面目愈發模糊,無法確定所演的角色甚至本來身分。加上演出全部使用國語,「澳門」歷史地域文化以至演員自身的語境,都明顯缺席或被同質化。一幕幕看似寫實的片段,卻沒有什麼能與我們真實生活產生聯想的細節,在一個強調兩地(台灣與澳門)共製的作品中,感覺只像看外地演出。一幕幕精心擺弄的場景好像想留下一些線索,但製造的失焦卻似乎更多。
有一些五分鐘不到的段落,有如一張硬照或一個電影定格畫面,沒有台詞只有姿勢造型,每一幕都由被稱為「造夢者」的演員純熟地快速轉換,過程甚至緊密配合音樂節奏,組合物件傢俱的次序步驟明顯經過嚴謹排練,俐落有致的換場成為整個演出中最亮眼的部份,高明的物件組裝也使人讚嘆強勁的舞台設計和道具製作團隊,然而如果「換景」本來就是演出的內容之一,就如隱藏其中的戲中戲,那麼當中每一個物件的出現和組成,包括它的顏色、材質,例如那張一分為二的床,是否都是重要內容?理應予以解讀?
然而,演出的多個技術問題又妨礙了解讀任何暗示的可能。「文化中心小劇院」中觀眾與演區相距較遠,不少台詞因為音量偏細,或者被滿滿的音樂與聲效蓋過,以致難以聽清,加上全國語演出卻沒有字幕,估計是因為已有用作翻譯伊朗詩句旁白的字幕(但為何是伊朗詩?為何是伊朗語?)由於旁白密度很高,字幕出現頻繁,投影有時模糊不清,所選字體又太幼細等,使人很快便放棄閱讀字幕。這些技術干擾都增加了對演出投入和理解的困難。碎片化的藝術形式由於失去解讀的脈絡,變成像要考驗觀眾耐心似的,製造了一場含混不清和重複拖沓的夢魘。
各種疑問無法在演出當中找到所指,只有產生更多不解和困惑,糾結成團,使人疲乏,彷如我們生活中無數快速閃過、可有可無的「符號」。所有的語言、動作、角色、場景,最終沒有引領我們的想像通去什麼地方,反而相互堵塞了解讀的可能,把生命的浩瀚化成一些表象的建立,純粹的鏡花水月,更是使人無比納悶。
總導演在場刊中提及現世的即食文化,發出「一切事物都在快速移動變化」的慨嘆,同時指出這個演出正是要「停下時間去感受」。然而諷刺的是,現在所呈現的作品本身,就正好是「快速移動變化」的示範,密集式的旁白和當中的感情泛濫,甚至有文化硬塞之嫌。令人擔心的是,作品引起不少關注,同時它的影響力也愈大:觀眾害怕成為懷疑者,卻對追尋意義產生倦怠或只是簡單歸類(如有人說是「法式浪漫」,這又是另一種文化誤解與歧異),另一方面,論述空洞也會使意義彼此消解。
到了今天,人們無時無刻都在進行著文化「啟蒙」和「交流」,不同文化經常無孔不入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當文化的「交流」、「滲透」,甚至「掠奪」變得如此交雜不清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沒有了自己的聲音、態度和立場,甚至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判斷。當自己面目變得模糊不清的時候,我們所需要的,又是哪一種的文化交流?
三地劇團歷時三年而育成的《鏡》,背後誠意無庸置疑,正如場刊中不約而同所說到的「追夢」。劇場是個夢,但在實踐的路上從不遠離現實,所以才值得追求。
*2018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評論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