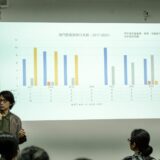記憶政治的「路.遊.戲」
春雨初霽,潮水漲滿,濤聲陣陣。「參與」《路.遊.戲》,沒有比在這樣的天籟之音下更適合的了。
一個到路環各處「遊」覽兼觀「戲」的「活動」,或者,劇場(?)
真的,遊.戲得很開心,最起碼增長了知識,比如「拍拖」詞源,比如火紅年代的路環民情,比如造船工會與信義福利會,比如沙紙契,比如造船知識與船廠日常。
更何況,造船廠裡的濤聲非常動人。
不過,跟著「戲」在路環各處遊走之時,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歷史」與「戲說」,再之後便想到「記憶」與「政治」。
在解構荒原的後真相時代,歷史到底是什麼?其答案越來越模糊,即使歷史學家也越來越沒有底氣敢說我筆下的就是真相。一切,不過是剪剪貼貼的敘述,而已。歷史學者,不過是把「故事」敘述得好的人,吧?而劇場作者,不過是把「歷史」敘述得動情的人,吧?
所以,一切,便可以以「戲」來「說」?
《路.遊.戲》很像後真相時代的「歷史」,彷彿源自真實/相,卻披了件戲說的劇場外衣。這是歷史的真實,還是過去的掌故?抑或,這是戲劇化的旅遊導賞?
一切都是漿糊剪刀,歷史學者選擇他的史料文獻,劇場作者選擇他的口述掌故,歷史學者尚需要擺出論文起承轉合的理性邏輯推演,劇場作者不需要論證推演只需要拼貼「此處應該有掌聲」(?)因為,劇場不是歷史(?)因為,劇場是感性抒情(?)
所以,祈求海上平安,竟然捨近在咫尺的水神譚公不求而去求土地公還要擲筊占卜?
所以,路環一早是國際旅遊城市?
所以,有商有量各退一步便是「路環精神」?
所以,足以用博士論文篇幅去討論的沙紙契便是「唔知佢講乜」「我住係度喎」的「唔使理佢」?
所以,一切政治議題便成了一片即將「消失的風景」?一段「有溫度」的敘事?
所以,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的記憶都是當代記憶?
是的,歷史與記憶,都是政治。
是的,當你的題材是沙紙契與船廠保育,那便是政治;你的記憶,你的遊與戲,便也是政治。當劇場選擇了政治,記憶便也選擇了政治——一切為自己的利益而選擇,而訴說。劇場人也成了政治人。
政治人不一定是壞人。不要污名「政治」。
因為劇場有了政治,或者,劇場預設了政治,劇場便有了選擇性的敘事拼貼——在整個路環的「歷史」中,為什麼選擇了這幾個片段?選擇性的敘事,便沒有了政治中立,但據說保育是政治正確。
劇場的聰明是,把政治議題變成一片即將消失的風景,記憶政治也成了懷舊情感行銷——有溫度的故事VS冷漠的權力。所以,世上只有最笨的政治人才會漠視劇場人。世上只有最笨的政治才會無視文化。
所以,《路.遊.戲》的記憶政治是成功的。尤其有那嘩啦啦的海浪聲來吶喊助選之時。
我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