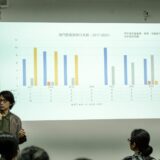2022觀演筆記(上):音樂劇場無限式、紀錄劇場的轉向、創作模式的反思
在一切貌似復常,但其實不再如常的2023,我想回顧一下2022看過的一些演出。
我去年看了38個演出,基本上與2021年差不多,以本地藝團或官辦節慶及系列活動演出為主,類型大致上是戲劇、舞蹈及音樂類演出。戲劇演出佔了23個,舞蹈及音樂演出則是15個。官辦(由政府部門直接主辦或出資的)演出有10個,約三分之一。在文化中心上演的有11個,在黑盒劇場演出的有或非劇場演出的有14個,其他非劇場空間(特定區域、商業空間及線上)的則有13個。沒有看的演出大致是學校或藝團的展演或比賽、大部分音樂類演出、親子演出、博企舉辦的各類演出活動等。
比較印象深刻的一些現象如下:
1. 音樂劇場無限式
就算我不是音樂類演出的常客,今年看過的音樂劇、音樂劇場及音樂演出共有6個,包括Water Singers令人期待原來在大場舉辦的《誰與水唱》、由澳門文化中心於疫情期間徵集的音樂劇演出《宜民傢俬店》、閒人公社及埋欄文化主辦的Guia Experimental實驗音樂節中的音樂與影像實驗、澳門敲擊樂協會的年度演出《十六擊》、兄弟班藝術會的音樂劇《北緯22°咖啡店》,及埋欄文化主辦的音樂及現場影像演出《外面好大風》等。
基本上這六個演出已涵蓋本地音樂演出光譜中常見的類型。以流行度作為坐標,《宜民傢俬店》及《北緯22°咖啡店》屬於大眾認知的音樂劇演出,兩者均將角色置於一個特定空間內,藉著角色之間的互動及其背景,或談情,或說愛,演員們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如霍嘉珩可男可「女」可麻甩可婆婆的演出水平,如馬曼莉演唱俱佳的亮眼表現。在澳門做音樂劇的問題是澳門沒有一個源自/借用當地的強勢流行文化,準確一點說,澳門的流行文化是借了歐亞多地流行及中國內地的傳統表演而來的。另外,澳門沒有利潤導向的強勢電視或流量媒體創造及輸出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商品。《宜民傢俬店》的音樂借用了耳熟能詳的曲子,所以相對能打動觀眾;《北緯22°咖啡店》在數年前的基礎上發展,人物的形象及故事相對扎實,但音樂就沒有熟悉感。最後,娛樂是一件很難做的東西,因為可對比的對象太多了。這個範疇的觀演水平其實很高,只要沒有特點或劇本沒有打動人心的部分,觀眾很容易發覺問題,並直接反映在反應中。
《誰與水唱》、《外面好大風》及《十六擊》則位於中間。它們都不以最大公約數的觀眾為目標,前兩者受眾為相對願意接受多樣化音樂演出的觀眾,後者則直接是藝團長期耕耘的學生及家長群。《誰與水唱》是四人女子無伴奏合唱組合Water Singers本來應於澳門文化中心的演出,但由於去年的文化資助政策出現重大轉向,最後自行於本地新興演出場地Bookand…Cafe舉辦的演唱會。也許是她們在劇場曾有亮眼的作品《音感》的經驗,在音樂編排上可見其考慮戲劇性。《外面好大風》同樣在前述場地舉辦,由音樂人及視覺藝術家共同演出,以多樣化的音樂類型結合現場影像的演出。《十六擊》則是常見的展演,由音樂人及藝團培訓的學生共同演奏敲擊樂,同樣有結合一些影像。後兩者都有結合影像,但成效一般,畢竟音樂與舞蹈都是類似的意象組合,也是在重覆與變化之間找到一個與聽者同步的律動,它們可以喚起觀眾的情感與記憶,但在敍事能力上不如以文字為基本載體的戲劇演出。
最後,Guia Experimental實驗音樂節的試驗則完全以形式的碰撞為重點。該試驗以電子音樂及從社交媒體擷取的影像並置播放。然而,於我看來,資訊爆炸或膚淺的題材已有太多討論,與其說是實驗,不如說是將音樂和影像的節奏嘗試組合成一個新概念,但也沒有甚麼特點。聲音的特點及主體沒有在實驗中出現,也難以解讀出甚麼。不過,能解讀聲音的人真的不多,就如本地表演藝術界對演出中的聲音論述幾乎為零一樣。
2. 紀錄劇場的轉向
紀錄劇場近年在澳門可算是蔚為風潮,由以各種群體的生活為基礎的演出,有時藝團會直接邀請貢獻前述藍本的素人直接擔任演員,如以女性家傭為主角的《迴遊》、以紡織女工的生活故事改編的《離下班還早—車衣記》、石頭公社近年一系列以身心障礙人士為主角的《世界和我怎麼樣》、《未境作業》及《未境作業.挫敗之慾》及移工群體經歷為藍本的《勞動的人》等。這類演出的特色是由演員/素人講述或表演作為觀眾共情或思考的起點或對象。
如果以文化生產及消費的角度看,此類演出其實與實境節目或商業紀錄片分別不大,只是它們最終達到的目的或娛樂或關注或共情,商業價值不能同日而語,但問題是一致的:實境節目需要找尋更能搏得眼球的「真實」題材給觀眾消費;藝人或一般人在鏡頭前表演「真實生活」;商業紀錄片的目的往往不是揭露真實,而是將「真實」變成某種可作為宣傳的內容。
將紀錄劇場放入此語境討論,是因為往往這些演出佔據了某種道德的正常性,從而模糊化了這個生產文化內容必定出現的過程。也唯有識認表演中的真實是按表演的框架經過修訂、過濾及選擇,最後在非原來生活的空間而演出,而無法企及那些被取材對象的「真實生活」本身,我們才能真正有一個共同的討論基礎:這些演出的「真實感」及「共情度」,而非因為這些演出基於真實故事改編或呈現,所以只要表演出不存在的「真實」,那些演出就直接獲得了一個更值得,也更不容批評的高度。批評的,是演出本身,不是為了創造這些演出所付出的心血,因為從觀眾角度,後者無從評價。任何創作這些演出的努力,可能都比不上那些甘冒生命危險報道濫伐雨林之惡或戰場殘酷而命喪黃泉的記者。
去年的紀錄劇場有石頭公社以女移工生活經歷為藍本的《消失的身影》及結合其藝團歷史及個人表述,並由三名成員各自擔綱重演的「獻給Frank的相對靜態版:《石頭外傳》(重演)」。另外,還有夢劇社與明愛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合作,以逝者及自殺者遺屬的真實經歷為藍本,由有親身經歷的人或參與培訓計劃的素人演出的《「《錐心之痛》—逝者、自殺者遺屬的聲音」》等。雖然今年的紀錄劇場較少,但在呈現方式的改變,非常值得一記。
《消失的身影》的呈現方式依循藝團一貫的表演方式及框架:勾勒大環境,輔以改編自訪談對象的故事作為表演內容,從中帶出一些需要關注的重心。對「觀看即關注」的觀眾而言,這類演出呈現的社會議題確有認識了一個澳門社會不同面向的新鮮感;對已經觀看此類演出有一段時間的本人,則產生了對此類演出的審美疲勞及對公共單位對各群體關注的,非關營利或消費目的的文化內容缺位的認知。《石頭外傳》重演年前搬演藝團發展史及個人經歷的同名演出,將石頭公社的編年史結合三位骨幹成員走過多年的個人感受,結合黃大徽導演手術刀級的導演水平,將「歷史」本身冷靜、簡約及巧妙地演繹出當下的體會,從而反思歷史與個人的關係。
《錐心之痛》則在劇場中成功結合了聲音及表演,以耳機將演出分成「個人」及「集體」兩部分。前段以各種真實經歷的拼接營造出逝者或自殺者的全景,各演出者的敍述聲音在耳機傳出,一人敍事營造私密的心音、雙人或多人疊音則調配情緒的濃度;後段觀眾拿下耳機,眼看演員集體演出的同時,輔以現場鋼琴演奏。演員集體演出,由部分演員講述失去某人的故事,其後演員匯聚成同一圓,每一張臉及眼神漸次接近觀眾。鋼琴演奏的曲目應是相同的,在琴師隨演出變化節奏的演出中,琴音的存在感更強,也更貼近情緒起伏。貫穿演出的是劇本及演出節奏的把控。打散分段敍事及起承轉合,將對白相互穿插,並由演員相互拋接,營造隨處可見的尋常感,以話語的音及質動情,而非以故事的高低階級、經歷悲哀而煽情,讓話語緩緩滲入感官之中。另外,散落的話語也織成一個支持網,讓各演員的故事有整體作承托。演出沒有撕心裂肺及社會控訴,觀眾隨著演員的敍述,就能逐漸拾起那些深埋心底,難以啓齒的回憶,眼淚就會不自主的流出。掌握形式的變化及有效地傳達給觀眾,是《錐心之痛》的強項。
3. 對表演藝術創作模式的強烈反思:「弱文本」
足跡於去年的演出都對「表演是甚麼?」這個問題提出一個可能的答案,而這個答案的嘗試在概念上是成功的,實踐上則仍與可跟多數觀眾溝通有一大段距離。如果前述目的不是藝團的目的,那就另當別論。與其他以類型演出為主的藝團各別苗頭,足跡在《嘉路士一世》及演書節的演出《藍色時分》及《繁漪4.48》中提出了「技術劇場」及「弱文本」的概念。
《嘉路士一世》是一個以光與聲作為表演者的作品呈現,觀眾在媽閣一帶及附近的海事工房2號劇場觀看其鋪設的聲音及視覺裝置。雖然技術及設定上有其巧思,以「人造環境」為演出主體,觀眾反為被觀看客體的思維也有其超前之處,但光及聲音的「語言」體系畢竟沒有文字的高度,在觀眾層面的反轉也缺乏,使作品變成一個典型的「當代作品」,即在多重思考後,各種形式的意義被消解後,使真實生活的人無從入手的作品。
演書節演出《藍色時分》及《繁漪4.48》則強調導演作為演出中心的退位,讓演出及台燈聲設計師等創作人發揮更多的創作模式。據莫兆忠(演書節特刊編輯、《繁漪4.48》戲劇文學指導,《藍色時分》編導)於特刊中提及:「『弱文本』的概念是從⋯『弱建築』的概念借來的⋯非指『柔弱』,而是藉由弱化建築功能性,體現對『他者』的接納⋯是單一所無法成立的局部在相互發生關係之下,彼此互相支持,藉由這種弱的連鎖,而成立一種全體帶有搖動的秩序⋯『弱』是這文本的領導權下放,強化表演者,以至各創作領域的選擇與創造,主動編織出各自的『演繹』⋯最終會導向一種美學上的選擇⋯」另外,「說故事」已常常不是劇作者的首要目的,「對話」也逐漸傾向獨白化⋯被視為補充說明的「附屬文本」,如舞台指示反過來決定了一個劇作的呈現方向。
《繁漪4.48》有三位女主演及台燈聲。三位女主演在演出前就在台上,演出開始時她們會交錯地唸出自己身處的空間、角色及行動。三獨白劇本表面上對自己角色的表述如《雷雨》強烈的寫實主義,內裏更多心理狀態則如Sarah Kane的劇作《4.48精神崩潰》(4.48 Psychosis)中遊走真實與虛幻之間的對白,如演員那些沒有意義的flash flicker slash burn wring press dab slash,就是直接挪用劇本而來的。她們之間錯落的獨白及動作,與配合其活動所需燈光及限制她們活動的白色圓形階梯舞台及置於其中的黑洞,構成了演出的全部。
沒有了主導演出的人,她們的演出模式與當今社交媒體盛行年代溝通方式類似:所有人在一個平台上對著一個未知的洞穴表達自己的感受,所以儘管每一個人的頁面都不可能是一樣的,且這些「內容」是演算法基於使用者的興趣及觀看紀錄作出推介的,理論上至少使用者可以理解其內容,就算是最膚淺的也好。然而,劇場不是臉書及Instagram,閱讀帖文、照片或影片時,還能夠一格一格地閱讀。在劇場,儘管內容可以被切成碎片,但觀眾的接收不能,那是實時的。而此時,這種呈現模式就出現問題了:互不重覆,編排上也沒有讓我感受到特定模式的對白,既聽不清、也很難從閱讀的角度理解對白的內容。文字、音律及其背後的象徵意義還是我認為很重要的部分。
前述問題更大的基礎在於「弱文本」的實踐有一個呈現邏輯上的問題。雖然弱文本的概念借用了弱建築中如洞穴一般,讓不同群體均能棲身的概念,然而,在演出中,演出與觀眾的位置沒有平等的空間。觀眾的視點被固定的位置限制,但《繁漪4.48》的重點與其說是看演出,不如說是在看一座大型的裝置或雕塑喃喃自語。我認為這個在創作上的意圖與觀看的可能性之間未能解決的鴻溝在於:要貫徹「弱文本」,那基本上就需要一個全新的觀演架構;現在的「弱文本」,尷尬地遊走在「表演」及「非表演」之間。
如是者,把文字、劇本及舞台元素都弱化到一個程度,我就會看其他的元素:演員、燈光、聲音及舞台。可惜的是,基本上這些元素脫開了文字及其象徵,單獨成章時無論是解讀或感受的空間大多差強人意。劇場的演出終究需要各個單位的投入及整合,弱化了這一塊,變弱的不僅是導演的權力,更是整體呈現的力度。
《藍色時分》是本地短片《見光》的延伸創作。後者的故事集中在男女莊荷的金錢、愛恨及生死糾纏的事件中,前者則以後者的女主角「慧慧」(由梁建婷飾演,其同時亦為《見光》的女主角)為中心,將她的生平、背景、動機及後續均仔細地描述出來,而《見光》的故事本身就作為《藍色時分》中快速口白的其中一段快速帶過。全劇為獨腳戲、配合舞台及近日掀起一道漣漪的匿名平台「我不?櫈——澳門劇場電影評論台」中獲多人討論的「彈琴佬」的現場音樂演出。整個製作我個人認為不太「弱文本」,基本上整個演出是圍繞著女主角的演出作為重心出發,所以才有這樣高度統一的配合。
因弱文本的概念而使各個形式浮上台面時,那刻意拉長的獨白尾音是最令我感到困惑而好奇的,導致我嘗試梳理了聲音的脈絡,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能夠貼近電視劇對話模式的戲劇演出一般較能讓觀眾理解,畢竟觀眾在聆聽上沒有任何學習曲線。然而,當超越了前述的範圍後,如何在創作及接收之間找(或不找)平衡,既是創作人的選擇,也是要如何讓觀眾在日常與日常之外,找到理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