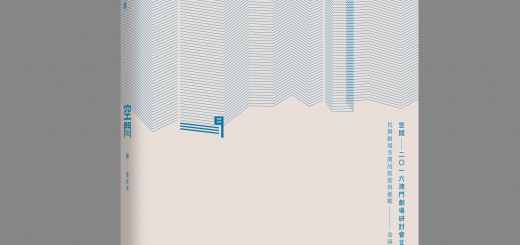舊的框架與新的敘事——談《我想行開吓⋯⋯》
破藝術的《我想行開吓⋯⋯》的前作在兩年前初次登場時,正值疫情限制旅行的時候,坐升降機獲取的「打折」飛行體驗,令作品極具噱頭,也成了時代見證。如今疫症變回了感冒,脫離了兩年前的關鍵背景,《行開吓》在基本保留原有形式框架的前提下,在敘事上明顯強化了內容量及深度,尤其是在「轉機」以後,關於澳門未來的想像部份。
《我想行開吓⋯⋯》在敍事結構上主要由兩部份組成,第一部份大致上與前作相同,觀眾由進入觀光塔開始即代入了乘客的角色,繼而坐乘藝術航空的班機,走訪五個主題各異的城市,分別呼應旅行中,關於文化節慶、大自然、色情、美食及購物五個面向,前作是使用觀光塔的客用升降機,每個「班機」只有兩個座位,且氛圍營造不算突出,基本上仍能清楚感知到目前所身處的,乃是升降機的空間。新作則使用了空間較大的貨用升降機,打造了一個能夠客納十多人的實景機艙場景,在「登機」上兌換機票的部份,也加入了vlogger及一般旅客等角色,遊走在觀眾周遭並進行片段式演出,大大增強了觀眾的代入感,兩個版本相比,第一部份的形式及內容變化不大,主要是表現力度上的增強。
第二個部份是《我想行開吓⋯⋯》版本新增內容的主要著墨處。在乘坐完藝術航空的班機後,創作團隊先是借角色表達對未來澳門的迷茫,再讓觀眾乘觀光升降機登上58樓,望著在當下澳門的夜景,以旅客的身份,用耳機聽著虛擬導遊用普通話敘述未來澳門的狀況,包括「托高」西望洋山以解決周邊限高問題,興建更多跨海橋樑,每天都有至少一個宗教慶典等等,而前作在到達58樓後,觀眾基本上是自由參觀。
和「藝術外賣」一樣,《行開吓》在處理表現形式上所施加的力度,要比處理內容的力度大得多,在《我想行開吓⋯⋯》中,創作團體顯然有深化內容以平衡兩者的取向,亦有見其成效,但總體而言敘事結構嚴謹性不足、焦點分散的情況依然存在,同時敘事維度與空間方向呈一致性的特點,也頗為有趣。第一部份的演出主要是在機艙場景中進行,機艙是一個狹長的空間,具有水平、橫向的特點,而敘事的時空背景也是當下,以飛行的方式進行空間移動(在城市與城市之間遊歷);而第二部份的演出,則讓觀眾目擊了觀光升降機垂直的空間移動模式,而敘事維度也由之前的共時異地,改為共地異時,變成了時光旅行。
演出雖然可以「旅行」這一概念串連起來,但事實上前後兩部份的敘事主題並不相同,前者探討的是旅行的意義,後者則是探討澳門的未來,兩者的轉換未免突兀,加上「轉機」的過程要通過一段長長的走道,才能到達觀光升降機,也令前後內容的轉接過於分明及生硬。
以一個大約時長一小時的演出來說,敘述兩個關連性不強的主題,焦點似乎過於分散,而且在某些表現手法上,也進一步分散或擾亂了觀眾的注意力。例如演出內容以碎片的形式串連或填充起來,尤其是第一部份,運用的象徵物太多且互不關連,實在讓人反應不過來;再來是距離及虛實的問題,第一部份是以實景為主調,但表達的內容卻是高度虛擬及抽象,例如載上黑超、穿上淨色緊身衣的大頭佛、像螢火蟲一樣發光的植物,還有頗為莫名其妙的人情味香水等等,但到了想像未來澳門的部份,主調是虛的,但內容反倒是實的,例如使用普通話的虛擬導遊,多建了幾條大橋等等。雖然也有如每天都有一個節慶,「托高」了西望洋山等的想像,但都具有很強的現實基礎,如「托高」西望洋山是建基於現行法例,當下澳門已經「幾乎」是每天都有一個節慶,這些論述都不帶有明顯的狂想色彩。
要育成一個成熟的作品,需要高昂的成本。《我想行開吓⋯⋯》比起前作有明顯的提升,但離成熟仍有一定距離,在主調及力度上的拿捏未得精準,在形式與內容上之間看見明顯的角力,但以重新製作一次的作品而言,算是不過不失。